今年以來,DeepSeek等杭州“六小龍”備受關注,引發各地城市對自身產業創新發展的反思浪潮,形成了產業創新發展的“杭州效應”。
“杭州效應”背后,一是外界紛紛關注杭州為何能誕生如此多的科創企業,二是跳出杭州看,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成為當前城市發展的一大趨勢。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走訪杭州余杭、濱江、拱墅、錢塘、富陽等產業強區發現,杭州在全國較早開啟招才引智體系化工作,又回歸市場邏輯,讓科創企業在適宜的產業生態中迅速壯大。經過優勢產業迭代,杭州科創產業集聚區的作用日漸明顯,良性循環的產業生態又吸引更多科創企業加入。
在杭州,城市與人的“雙向奔赴”,既有商業邏輯的考量,也有各自創新氣質的匹配。杭州民營經濟自發成長、數字經濟優勢明顯、創新試錯容忍度高,形成鮮明的城市口碑,一些早期科創企業選擇杭州,正是因為需要長期主義的創新環境。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史晉川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20年前,杭州沒有選擇重工業轉型升級路徑,而是抓住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科技革命帶來的創新創業紅利,形成互聯網產業的集群發展,為后來杭州轉向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產業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杭州的產業轉型形成一種特色路徑,首先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民營經濟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主體。其次,通過互聯網產業的集群發展,杭州集聚了大量的創新人才、社會民間資本,使金融創新、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相對能夠融為一體。”史晉川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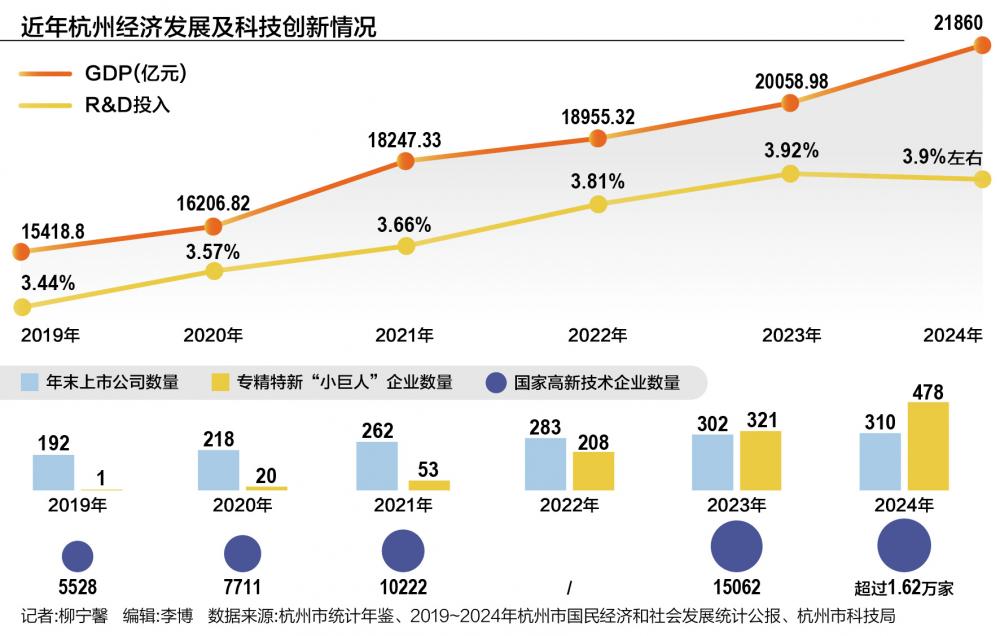
“科技副總”與“產業教授”
從互聯網到硬科技,杭州都不缺先鋒企業,這背后離不開人才的支撐。在國內眾多城市中,杭州較早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
杭州高新區(濱江)在全省最早推出高層次人才創業支持政策“5050計劃”,每年引進人才超4萬,人才總量超50萬。目前,杭州高新區(濱江)已經是浙江省數字經濟第一區、浙江省上市公司第一區,2024年全區實現GDP2887億元,已累計培育上市公司74家,擁有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100家,國高企超過2800家。
對于人才特別是本地高校創業團隊來說,杭州科創轉化氛圍與創業者十分契合,體制機制的創新讓科研人員創業少了顧慮。杭州“六小龍”中,三家企業創始人出自浙江大學,分別是云深處董事長兼CEO朱秋國、群核科技創始人黃曉煌、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
在杭州生物醫藥港,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見到了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杭州捷諾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徐銘恩,如今他依然是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兼顧企業和高校的工作。
徐銘恩談起創業的初衷時表示,“十多年前,我們就覺得研究不能再放在實驗室的抽屜里,而是應該真正讓大家能用得上,就決定做產業轉化,科技工作推進到一定程度,也需要有新的體制機制去推動成果走出校園,經得起重復和檢驗。”
捷諾飛成立于2013年,在生物智造裝備、器官制造、高端生物材料與醫療器械等前沿領域不斷革新技術產品與解決方案,其自主研發的生物3D打印機已覆蓋國內近60%的市場,出口至多個國家。
“我覺得最好的環境是能讓技術創業者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去跨越創業的死亡之谷。杭州的市場競爭環境相對公平,以生物醫藥為例,上下游產業鏈也是暢通的。”徐銘恩說。
近年來,浙江積極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省級創新深化試點。今年以來,浙江加快實施高層次人才“互聘共享”計劃,從高校、科研院所遴選一批人才到企業擔任“科技副總”,從企業遴選一批人才到高校擔任“產業教授”。
早在10年前,浙江就推出《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條例》《浙江省知識產權保護和促進條例》,隨后逐漸修訂完善,構建起“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產業升級”的創新閉環。
浙江大學工業技術轉化研究院院長助理、浙大知識產權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總經理童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浙江大學師生校友創新創業傳統來源于求是創新、寬容失敗的文化氛圍,也基于制度化體系化的成果轉化鏈條。
“我們想以浙大為中心,在創新生態圈里齊聚各類創新要素,讓渴望創新、服務創新、正在創新的這些人圍繞周圍。同時,形成寬容失敗、良性競爭的競合關系,彼此之間要有交叉融合。”童嘉說。
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長期主義
客觀來看,杭州既非全國最早強調科創的城市,也不是科創資源最強的城市,但在科創孵化、政策創新方面杭州具有顯著的開創性。
在走訪過程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多數創業者都提出長期主義,一是創業團隊推進成果商業化、跨越死亡谷的長期主義,二是城市對于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長期主義,這需要多方資源參與、提供有效支持的創新生態。
3月17日,在“新智煥發看浙江”——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主題采風活動上,杭州高新區(濱江)區委常委、零磁科學谷(智慧新天地)黨委書記丁昌鈺提起“大孵化器”理念,即鼓勵成功、寬容失敗,耐心陪伴高科技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易思維(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在杭州成立,來自天津的創業團隊在杭州繼續生根發芽,2018年又成立北美子公司。作為汽車制造領域機器視覺技術的先鋒,這家企業與海內外頭部新能源汽車企業合作落地數十類應用場景,參與了超1億輛成品汽車的制造過程,近年來業務也擴展至軌道交通運維領域。
易思維相關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企業在做融資的過程中,通過一家投資機構接觸到了濱江區政府,雙方一拍即合,企業便決定到杭州發展。
易思維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初選擇落戶杭州還考慮到,一方面,企業做機器視覺行業與濱江視覺產業鏈十分契合,另一方面,長三角有很多汽車制造客戶,視覺產業人才也很充足。“我們想更貼近客戶、更接近人才。”
中昊芯英(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是海歸創業團隊在杭州發展的一個縮影。
中昊芯英是國內唯一掌握TPU架構AI芯片核心技術并實現TPU芯片量產的行業領軍企業,其創始人楊龔軼凡在谷歌TPU核心研發團隊工作過,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和技術背景。2018年底,楊龔軼凡帶領海歸創業團隊回國創業,并于2020年正式在杭州注冊落地,開始了企業的快速發展期。
在杭州的五年間,中昊芯英實現了從初創到快速發展的蛻變。目前,中昊芯英也是初創芯片公司中少數已實現盈利的。其全自研的高性能TPU人工智能芯片“剎那?”,在處理大規模AI模型計算時算力性能達國內頂尖、國際第一梯隊水平。
楊龔軼凡告訴記者,當初回國創業時的擔憂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創業的細分方向在國內是否能夠有人支持,二是對國內環境不熟悉,不知道哪些城市適合企業發展,有好的產業生態。
楊龔軼凡表示,在早期,研發時間長、產業生態還未形成,企業發展需要耐心,也需要資金和資源的支持。早期資源基礎比較薄弱,是海歸團隊回國創業常見的一種現象,需要資源和資金的“雪中送炭”。
“畢竟芯片產業的研發、量產資金門檻很高,多是以億元為單位的資金投入。我們通過自己的力量,其實很難去協調更多的社會資源。”楊龔軼凡說,在2020年大家對大模型還沒有概念時,浙江省政府當時就有很強的眼光,非常支持企業在這里發展。
“當大多數地方還在關注畝產稅收、工業產值時,浙江已經以人才為本,通過評審人才、提供配套政策等方式,為中昊芯英等科技企業提供了寶貴的支持和資源,支持我們去完成一個完整的AI芯片研發。此外,浙江豐富的科技企業和產業生態,也為中昊芯英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我們在杭州的5年,能感受到這邊芯片設計、生產的企業都在增加,濱江區科技公司密集,上市公司眾多,這個地方的確非常適合科技創業者。”楊龔軼凡說。
從杭州全市來看,2004年修訂實施的《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條例》,在全國率先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明確“每年從財政支出中安排不低于15%的比例設立產業扶持資金”,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活動。
今年,杭州提出了“三個15%”的科技投入政策:市財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長要達到15%以上;市本級每年新增財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統籌現有產業政策資金當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
杭州產業集群迭代之路
對杭州而言,創新生態與城市自身產業轉型之路緊密相關,在此前互聯網產業集群發展中得到有效驗證,如今又適用于高科技領域的創業孵化。
20多年前,杭州曾經強調“工業興市”,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給杭州帶來了一次發展的低谷,隨后5年,杭州發展工業受到土地、資源制約越來越明顯,發展路徑有待轉型。
2014年,杭州開始全力推進信息經濟優先發展,同樣在這一年,阿里巴巴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2017年,中國(杭州)人工智能小鎮正式啟用。2021年,杭州市“十四五”規劃明確定位杭州為“數字經濟第一城”,同年,《杭州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杭州要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工智能頭雁城市。
2022年,杭州提出打造智能物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和綠色能源五大產業生態圈。2025年,杭州又在培育未來產業行動計劃中明確通用人工智能、低空經濟、人形機器人、類腦智能、合成生物等五大風口潛力產業。
具體到產業強區,杭州未來科技城正在建設“1+3+X”未來產業體系,重點發展未來網絡、人工智能、空地一體三大標志性產業;杭州高新區(濱江)拉開了“一園三谷五鎮”產業布局,“中國視谷”“國際零磁科學谷”“中國數谷”都是產業集聚的特色品牌;拱墅區則圍繞“1+4”主導產業,以及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新興產業,制定“1+4+N”產業政策。
史晉川表示,20年前,杭州在大量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產業需要轉型升級時,沒有循規蹈矩做重工業化的轉型升級,而是抓住了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這一波科技革命帶來的互聯網創新創業紅利,形成互聯網產業的集群發展,為后來杭州轉向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產業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這種產業轉型升級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非常重要的案例,也使民營經濟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主體。”史晉川說。
在史晉川看來,杭州也因此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形成一種特色路徑,通過互聯網產業的集群發展,集聚了大量的創新人才特別是技術人才,也集聚了大量的社會民間資本,打造了一個比較領先的創業投資市場、早期投資市場,使金融創新、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相對能夠融為一體,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如今,新興產業集聚區在杭州各區星羅棋布,配套的產業體系、政策配套、轉化平臺日漸完善。
在拱墅區,智慧網谷小鎮便是從老工業倉儲基地變為數字經濟新興產業集聚地。“中國醫藥港”核心區的錢塘已集聚生物醫藥企業1700余家。富陽區引進杭州光機所、西湖大學光電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級科研院所,做強集成電路、光電激光、生物醫藥、智能汽車核心零部件等新興產業轉化平臺。
以科創拓展城市經濟的寬度
在3月15日的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經濟增長可以從兩個維度看,一個是經濟增長的高度,另一個是經濟增長的寬度,所謂高度比如搞創新、搞對外開放、搞改革,都是在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把整個空間向上擴張。
當前,眾多城市把創新提升到重要維度,想要抓住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變革機遇。
在走訪過程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杭州不少科創企業對產業方向的研判都是站在科技創新作為生產力的維度上,期望從不同面向拓展未來發展的增量空間。
八維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空間智能技術研發與行業應用的企業,推出了自主研發的空間智能平臺“BWT-Urban”,創新性地引入ViLSP(Vision Laguage Spatial Physics)即視覺語言空間物理大模型技術,為大模型嵌入了對三維空間和物理規則的理解能力。
八維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數字官鄭航介紹,八維通使用大模型加物理引擎的訓練方式,可以做到實時云端訪問計算,快速搭建空間模型,目前已用于消防領域的火災預警,也可用于水災現場、體育場人員疏散等真實場景的模擬計算,得出最優解。
八維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宏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企業2019年就開始做空間智能相關領域研發,當時的想法是人工智能對物理世界要感知、互動、做決策,必須要對空間進行建模,目前在水利、消防應急已經有應用,“例如,我們為機器狗裝上‘大腦’,讓它可以對空間進行識別,進行消防場景的巡檢。”
楊宏旭認為,要創新必須形成差異化優勢,需把握產業政策導向,也要深挖行業痛點,杭州搭建特色試驗場供企業試錯,也會對創新研發提供資金支持推動技術轉化,提供了很好的創新土壤。“隨著技術浪潮推進,人工智能的馬拉松剛剛開始,我們現在先卡好位,基于場景應用迅速整合新技術創新。”
對城市而言,如何以科創拓展經濟發展的寬度?
杭州市科技局局長樓秀華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杭州要做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首選地,鼓勵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原始創新研發技術到杭州來轉化,實現產業化,就像此前的地瓜經濟。
在杭州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看到讓科技成果“從1到100”平臺實踐,杭光所由地方政府支持,匯集一批頂尖科學家,構建起了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算法(科創生態)+數據(科技成果)+算力(基地)”科創孵化模式,將硬科技前沿技術進行創業轉化。
目前,杭光所已孵化50余家硬科技創業公司,吸引外部社會資本超25億元、孵化企業總估值超250億元。
杭州光機所副所長趙虹霞向記者介紹道,科技創新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解決好科創的發展和安全問題,關鍵在于把“新質”的勢能轉化為“生產力”的動能。杭州光機所提出“創新—創業—創投”,打造根據地式的孵化器,構建最懂科學家創業的孵育體系,讓硬科技產業化少撞南墻。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新質生產力不能僅僅停留在概念的認知之上,要有項目和主體產業,要有規模和利潤,包含豐富內容的系統工程。
“在原有浙商全球網絡基礎上,可以增加創新的新內容。例如,和外地高校、科研院所、企業機構建立更多聯系,共同搭建跨地域研究平臺、創新飛地。”曾剛說。